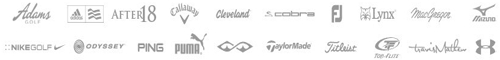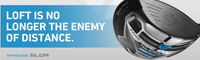|
“赛事多的时候每个月有三场,不过冬天平均一个月也出去不了一场。”一名裁判介绍说。记者问他家住在哪里。“没有固定住所,比赛在哪里举行,我就去哪里。”这个回答着实反映了国内裁判的生活状态:开始跟着比赛跑,后来找到较为稳定的工作,把裁判作为兼职。但这也会出现新的矛盾:出来执法的机会变少,要以日常工作为主。 2010年5月,朝向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赛事部员工董文明收到亚组委的邮件,邀请他去当高尔夫比赛的国内技术官员。他向公司请假很顺利,副总经理孟涛拍板:“这是好事啊!多出去看看,学习学习吧!” 并不是每个裁判都像董文明那样幸运。国际裁判小A以前在南方一家球会工作,2009年中高协通知他去当沃尔沃中国公开赛的裁判。这是中国最高级别的高尔夫赛事之一,选手水平高,裁判阵容豪华,小A当然兴奋难耐。但是,小A的主管却拒绝在他的请假报告上签字,理由是会影响他的本职工作。小A怎么做领导的工作都不行,最后愤而辞职,还是去执裁沃尔沃中国公开赛。 和小A有同样尴尬的裁判还有很多,很多。陈盛炽2006年大学毕业后来到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当老师,现在是旅游与酒店管理系高尔夫教研组组长,主要教授高尔夫概论、规则、球童学、专业英语等课程。只要他愿意,周周都有机会出去当裁判,但是,校领导只同意他一个月出去一次,而且不能影响正常教学,去之前调课,回来后补课。 陈盛炽对此已经心怀感激:“我们学校培养‘双师型’教师,既懂理论知识,又有实践技能,所以校领导鼓励我出去当裁判,一个月请假一个星期都能批准。我也很理解,毕竟还有那么多课在那儿摆着,假请多了回来都来不及补。”受陈盛炽的影响,他的学生也大批去考裁判。单是2011年,他们班上就有3个学生通过了国家级裁判考试。 顾军以前在金鸡湖球会工作时,也是一个月只能出来执裁一次。遇到2008年经济危机,他所在的运作部裁员,留下的员工承担的工作任务一下子加重,他请假就更难了。现在,顾军在广州和朋友一起做生意,去中、小学推广高尔夫普及课程。由于工作时间弹性大,再加上老板是高尔夫发烧友,对规则也特别有兴趣,见到顾军都喊“顾老师”,没事就拉着他探讨案例,请假就容易了很多,老板甚至说没必要和他打招呼。尽管如此,顾军一个月最多也只出来跑两场比赛,“我总还得兼顾一下家庭生活吧!” 更让裁判们纠结的是,他们还不能总是对中高协抛出的橄榄枝说“不”。国家级裁判小B说:“一次、两次不去没什么,如果我们拒绝的次数多了,以后可能就很难再接到中高协打来的电话了。” 相对而言,去高校当老师就成了裁判们最理想的工作。一是老师这个职业稳定、社会地位高,二是老师还有个寒暑假,接到中高协的召唤可以拔腿就走。 水平高的裁判都找到了“下家”,但是能外出执裁的时间非常有限——这样的状况造成了目前执法国内赛事的多是“学生军”。这些学生裁判大多来自深圳大学、吉林大学珠海分校、暨南大学深圳旅游职业学院。因为学生的自由时间比较多,而且他们也需要实践经验。不过,一名资深裁判不无担忧地说:“目前国内裁判高分低能的比比皆是,他们理论考试的成绩好得惊人,但是真正能下场执法的寥寥无几。他们最多也就只能做专业性略微弱一些的赛事秘书,负责分组表、通知、成绩、排名、洞位图等。 ” “赛事太少,裁判太多,”一名在球会从事赛事工作的裁判直言,“目前中国不可能出现欧美国家那样的全职裁判。”在美巡赛和欧巡赛,裁判隶属巡回赛组织,相当于公司的员工,他们按月、按年领取薪水,而不是像中国裁判这样一场一场“打零工”。 记者曾采访美巡赛的工作人员,询问美巡赛的裁判生活是怎样的。对方回答,一年至少30-40场比赛,裁判已经忙不过来了。 2012年已经是欧巡赛裁判长约翰-帕拉莫(John Paramor)为欧巡赛工作的第35个年头,刚过完21岁生日,他就成为了欧巡赛的一员,直到现在。 目前国内一部分裁判在赛事公司担任赛事总监,孔维东也是其中之一,他在2010年年底加盟了中体旅(北京)体育发展有限公司。另外,有一部分裁判加盟了球会,还有的在做球场改造、练习场改造生意;有的转行成为球场建造专家……五花八门,不过他们都承认,裁判工作让他们得到了很大锻炼,对职业发展还是有一定帮助的。 但是另一方面,这些积累了一些经验的优秀裁判都转行了,裁判人才流失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“裁判行业的现状是人才一直在流失,一直在培养,整体水平总是无法提升。”一名业内人士不无担忧地说。 |